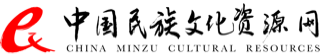从走廊发现中国·河西走廊篇 之一 从河西走廊看“多元互构”
中国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创造的,其历史呈现“多元一体”的发展轨迹。中国的多元性,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相关于地理—气候—生态的复杂性,中华大地的平原、草原、绿洲、高原等各种自然生境,是生活于其上的人群造就和分衍出不同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又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进程的复杂影响。“多元”之间有着长久而深刻的互动过程,它们互为条件,相互影响,在历史进程中共生演化为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多元亚区域之间由若干个走廊地带相互衔接,相互嵌入,这些走廊地带或过渡地带,是“多元”得以具体链接的历史—地理—文化基础。同时,这些走廊地带在历史演绎的过程中,又逐渐成为区域单元或中国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走廊地带,能够发现“多元共生”体系的历史进程、演化逻辑和动力机制,是我们理解“多元一体”的中国的重要切入点。
这样的走廊地带或过渡地带,并不同于今天的重要交通线或省区毗连地,而是历史上在沟通区域板块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通道。这样的走廊地带或过渡地带相关于不同的地貌与生态区位,也相关于地缘政治关系的改变,在不同历史时期过渡地带的范围与重心也不尽相同。
为此,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推出了《从走廊发现中国》大型专题。河西走廊作为中国唯一的同时衔接起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与青藏高原这四大亚区域的走廊与过渡地带,是我们观察中国多元互构,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切入点。我们的这一专题将以河西走廊的系列讨论作为开篇,从这里发现中国。
一、 河西地理与古代中国秩序
王剑利:我来自中国的最西北边陲,那里横亘着高大的天山。农民和牧民就在山脚和山腰守望、共生,他们能深刻地理解对方。从天山一路向东,进入河西走廊。这条狭长的绿洲连缀地带,犬牙交错地嵌入到四个区域板块中,它夹处在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与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走廊北山之间,从西域向东延伸到黄土高原。游牧和农耕的族群从不同的山川孔道进入河西走廊,往来穿梭,他们既共生于此,亦彼此互相理解。这是河西走廊的历史和地缘使然。在河西走廊,我很自然地就对农牧共生、民族交融的社会生活有种文化直觉主义的熟悉感。因此,带着对这方土地的亲近与敬畏,我试着对它达成一种“移情式理解”。
施展:我再尝试从政治学角度来讨论。
我们在上一篇笔谈中进行过东西方对比。对西方世界来说,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当性的问题;而对东亚大陆包含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青藏高原等多个亚区域的这个体系来说,历史上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这些亚区域之间,尤其是作为秩序主轴的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之间,如何找到一种秩序安排,以便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
持久和平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有能够衔接起各个亚区域的过渡地带,或者说走廊地带。在政治空间秩序的意义上,走廊地带才是定义中国的基础所在,它们使得作为体系的中国,真正连接为一体。河西走廊是唯一的一个同时连接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绿洲与青藏高原各个方向的过渡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河西走廊才定义着中国。
我在《枢纽:3000年的中国》一书中详细讨论了农耕与游牧的共生关系。这两种生产方式之分,首先是基于气候差异带来的自然资源约束。这种气候差异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有着不同基础。东部地区的气候差异主要是基于纬度差异,西部地区的气候差异则主要是基于大山所形成的海拔差异。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东部地区的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主体彼此分离,少有空间上的交错,农牧两个群体不大容易相互理解;而西部的这两个群体,就如同你的生活体验一般,在山脚和山腰日日相望。相互就能较好地理解。所以在东部的游牧者入主中原之际,却经常需要西部的人来帮助进行治理,因为西部的人能够同时理解农牧两个族群的秩序逻辑,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重要粘合者。
王剑利:当我们策划《从走廊发现中国》这个专题时,注意到了你在《枢纽》一书中对“何谓中国”的思考,书中展开了从过渡地带讲述“多元互构”的体系史的思路;我们同时也有幸与数十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关注不同走廊地带的学者探讨走廊地带对于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这些研究与讨论都带给我们重要启示。
我们的专题从河西走廊开篇,正是因为河西走廊确实在深刻的意义上发挥着你所阐述的这种多元互构性的作用。它对四个亚区域的衔接性不仅仅是在地理上,更是在文化上的。单纯的地理无法形成历史,它需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形成历史,而人的活动,又必须通过文化才能形成意义空间,从而自我组织起来,历史才得以展开。河西走廊作为重要的过渡地带,使得其所衔接起来的四个亚区域,可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相互激活,从而使得作为一个体系的中国,能够获得生生不息的内在历史动力,不断共生演化。
施展:秩序和文化想要展开,首先要面临地理这个硬约束条件。
人们通常认为河西走廊的东段起自位于兰州与武威之间的乌鞘岭。乌鞘岭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该山脉以东是季风区和外流区域,以西则是非季风区和内流区域。河西走廊的南侧是祁连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积雪,雪山融水浇灌了山脚下的多片绿洲,有些地方水草相当丰美。比如山丹县历来就是重要的马场。霍去病攻占河西之后,匈奴人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便是指这里。河西走廊断续的绿洲,成为从中原与西域交通线上的一个个中继站。
祁连山脉有几个重要的山口,是历史上南部的高原游牧族群进入河西走廊的通道。走廊北侧的山脉则海拔相对较低,难以存住积雪,于是山的外侧便是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祁连山上的融雪流下来,自东向西分别形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这三大内流河水系。由于山形地势的原因,这三大水系都是中国少见的南北流向,穿过戈壁沙漠,注入尾闾处现已近干涸的湖泊当中。而当年的草原游牧族群,常顺着这些水系南下,进入河西走廊的水草丰美之地。
我们在上一篇笔谈中谈到的古代中国的外部均衡与内部均衡,在河西就能极为直观地呈现。当各个亚区域处于彼此对峙状态,即外部均衡状态的时候,河西走廊就是中原与草原双方着力争夺的战略区。汉武帝西逐诸羌,不仅开始了中原王朝对河湟地区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农耕族群与高原游牧族群之间的冲突。对汉王朝来说,倘若蒙古草原与青藏高原两群游牧者联合起来,将对中原地区形成战略包围,对长安形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必须控制河西走廊以切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为控制河西走廊,又需要进一步经略西域。而当大一统王朝实现了内部均衡之后,能够连接起多个亚区域的河西走廊便一转成为王朝内部至关重要的一个过渡地带,让王朝所需的各种要素通过这里而被整合起来。
王剑利:河西走廊在地理上是一个连接四方的十字路口,同时又自成一域。有不少学者关注这一区域内各民族共生共育的历史。早在先秦和秦汉之际,戎、羌、氐、大夏、居繇,乌孙、月氏、匈奴等族就活跃在这里。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来隔断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实际上开启了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在河西走廊上深层互动的历史。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游牧族群在河西历史舞台上担任主角,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在进退之间,始终发生着交往交流交融。农、牧族群因地域相连所带来的冲突和摩擦又转化为一种深刻的“糅合力”。河西走廊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穿行在这里的各个族群,他们共同创造了河西,成就其沟通四方的历史。
从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来说,发生在河西走廊上的农、牧族群的互动,意义极为深远。每次冲突和对峙,实际上都会推动农、牧族群的凝聚与整合,整合的结果不仅体现于河西走廊上各族群、多元文化的共生演化,从长远看,又为后世在整个中国格局内的农牧互动、文化交融提供了动力和历史前提,并最终促进了中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二、河西走廊与“多元互构”历程
1、王朝政治空间结构的历史变迁与河西战略意义的流变
王剑利:“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历史上,河西走廊是屏蔽关陇、经营西域的门户与基地,是王朝经略天下的重要枢纽,如同“国之右臂”。但河西毕竟不是古代王朝国家的核心地带,其战略意义的具体呈现,还需要通过王朝政治空间结构的历史变迁来获得理解。在这一变迁历程中,河西走廊的战略意义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施展:政治地理空间的结构变化,一般来说都与安全问题的变化相关。要注意的是,王朝国家的安全与朝廷的安全虽然在本质上并不可分,但其侧重点却不一致。
从汉到清的历史中,“唐宋之变”是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王朝国家内部多有世族强藩,中原王朝北部的草原强敌虽然对王朝安全构成威胁,但对朝廷来说,其首要威胁来自王朝内部的强藩。比如,刘邦在刚得天下的时候想要定都洛阳,张良强调关东的强藩是朝廷的大威胁,劝服刘邦定都长安。而如果世族太强,皇上已无力压制,只能选择与他们合作共治天下,就会定都在世族的大本营。东汉以及魏晋定都洛阳,大多出于这一考虑。后来隋唐的强藩大本营不在关东,而在关中,对君主来说,洛阳与长安的意义就正好反过来。汉唐间王朝的政治空间结构始终以“东西关系”为主轴,国都不出关洛地区。
在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对于王朝来说性命攸关,因为它离国都太近了,一旦河西有失,国都将直面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因为靠近国都,河西的战略意义显著,其族群格局、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变迁,对于王朝的影响力度也是极大的。
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开启了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此后,王朝国家内部渐无强藩,对朝廷来说,北部草原上的强敌则成为主要的威胁。于是,王朝国家的政治空间结构的主轴就从“东西关系”转换为“南北关系”。其首都也相应地转移到长城沿线地区,倘是中原农耕王朝,则以此来防备北患;倘是涵盖中原-草原的二元王朝,则以此控御两边。由于从辽代开始的二元王朝皆起自东北,这也就决定了,只有定都北京,方可形成对中原、草原、东北的多方控御。
北京与河西相隔千山万水,河西的形势对王朝的安全而言就不再是性命攸关了。但是王朝若想达到一个超越于草原-中原之上的持久和平之秩序安排,则必须以河西为中介,衔接起各个方向。河西的战略意义,就此也发生深刻变迁;而河西的族群格局、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发展,也以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方式影响王朝秩序。
2、文武之道——河西学脉的流传
王剑利:你的分析,把河西走廊的历史地理置于一个宏大的时空格局中,可以解读出很多意义。我们还可以讨论河西走廊之所以成为过渡地带的历史进程以及发挥“多元互构”作用的动力机制。这是个很大的议题,我们的专栏学者从不同角度可能都会有所呈现,相信其整体机制也会在此学术互动过程中浮现出来。
河西走廊是历史上农耕和游牧对抗、互动的最前沿,也是移民屯田戍边的主要区域。自西汉锐意经营西北,河西就成为一个农牧交错的多族群交往地带;同时,河西走廊是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的主动脉,是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融汇的通道。从西汉中后期起,河西的文化由边荒转向繁盛,成为崇文尚武之地。边塞冲突与战争、东西文明沟通与融汇,过渡地带的特殊环境历练出了河西走廊的“文武之道”。汉朝的河西走廊出现了大量“文为儒宗,武为将表”的两用人才,谙熟“羌胡习性”和地理,既能驰骋沙场,亦能讲学论道,文武传家。张掖城区水溪的主要源头甘泉,自城南分为文流和武流两翼,汇合于城北,在城北的甘泉遗迹上就曾有题额“文武一道”。在我看来,文武之道,相得益彰,是河西学脉萌发、沿袭的独特生命力。
施展:这让我想起陈寅恪先生谈到的河西学脉对于儒家文化传承之重要性。晋室南渡之后,在河西走廊这里先后建立过被统称为“五凉”的五个割据政权,河西学脉就出于它们对儒家文化的保存。
魏晋之际,官学沦废,学问中心转以家族为载体。西晋末年,海内鼎沸,两京荡为丘墟,学问家族四处流散,除了逃向江左之外,相对来说隔离于中原,秩序安定、经济富饶的河西走廊也成了一个重要的逃亡方向。诸“凉”的君主有汉人也有胡人,但都很重视儒家文化。439年,北魏灭掉了最后一个“凉”国,河西学脉也就被北魏所吸收,成为它极重要的文化来源。甚至影响到北魏后期迁都洛阳这种重大决策。
要理解河西学脉,还有个重要的现象值得关注。历史地理学者李智君的研究发现,河西走廊那些传承学脉的大族,主要是自西汉时期开始在河西本地孕育出来的。河西大族的出现,甚至比中原地区还要更早,也就让河西学脉有了更长的孕育时间。到了晋末天下大乱,中原学道废弛,河西学脉不辍,遂显出来了。河西更早出现大族,也许可以从政治经济学上作出解释。河西走廊在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绿洲贸易通道,绿洲贸易要横穿漫长的戈壁,条件恶劣,风险很大。除非有超额利润来对冲掉风险,没有哪个商人能够持续经营下去。垄断地位是带来超额利润的最简单手段。所以,我们看那些绿洲地区,通常都有几个垄断性的大商人家族,这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经济学结果。直到近代的交通技术获得突破性发展,绿洲贸易的风险性急剧下降,才能够打破这种状况。
在南北朝时代,读书是极其昂贵的事情,刘裕灭后秦入长安,接收的书籍不过四千卷,北周、北齐的宫廷藏书也不到四万卷。宫廷尚且如此,民间藏书的成本就可想而知了,故而学问大族必须得是财富大族才支撑得起。财富对学问虽不是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
河西学脉虽然盛极一时,到北魏灭北凉,迁走了北凉都城的主体人口,河西学脉便一落千丈。于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原的战争,却在河西的文化上形成一种活塞效应,推动着儒学西行,又拉动着它东归。但是,这其间的趋动力又是复杂的,还可以把观照视野放得更大一点。
王剑利:视野放大的话,还可以横向作个对比。依李智君的研究,河西学脉在东汉中后期走向繁盛,同时期的河湟谷地、黄河沿岸的塞上同样战事频繁,却并未如河西一般发展出文武并重的文化繁荣。由此可见,河西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与门户,因丝路的开拓而带来的东西思想汇流、多族群的交往互动,对各族风习、中外文明的兼收并蓄,为文武之道的塑造注入了超越中原儒学的多元基因。这种在过渡地带蕴养出的文化基因,不仅是该地域的多元文化共生繁荣的重要根基,反过来也成为刺激中原儒学成长演化的生命活力,也为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无限的潜力。